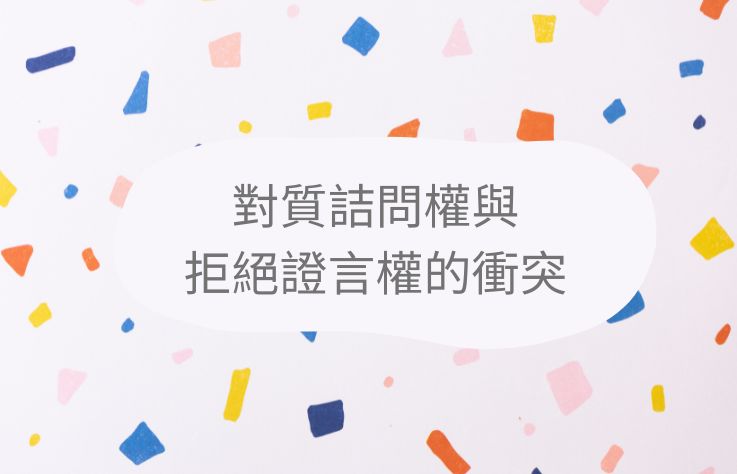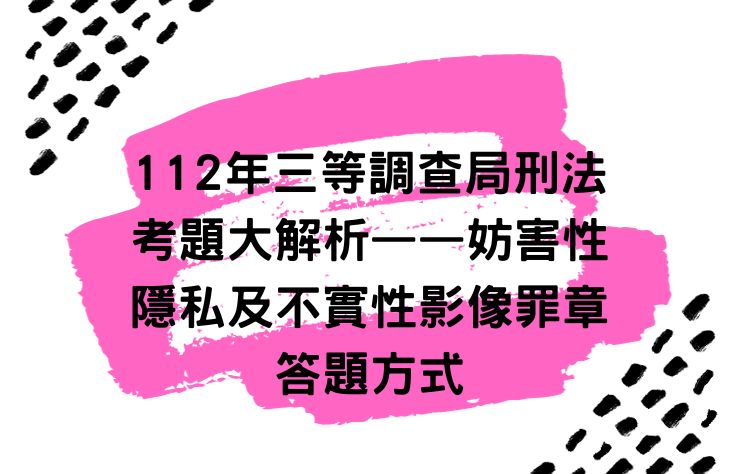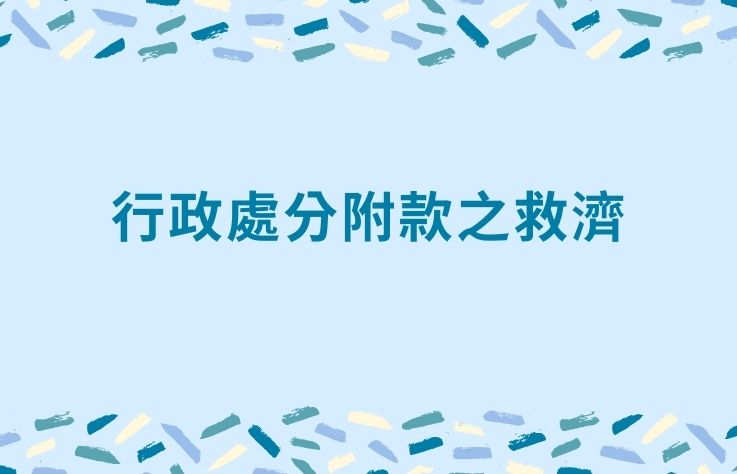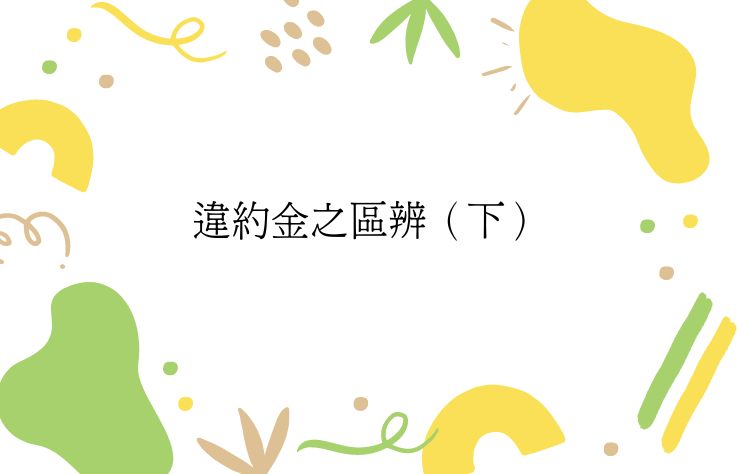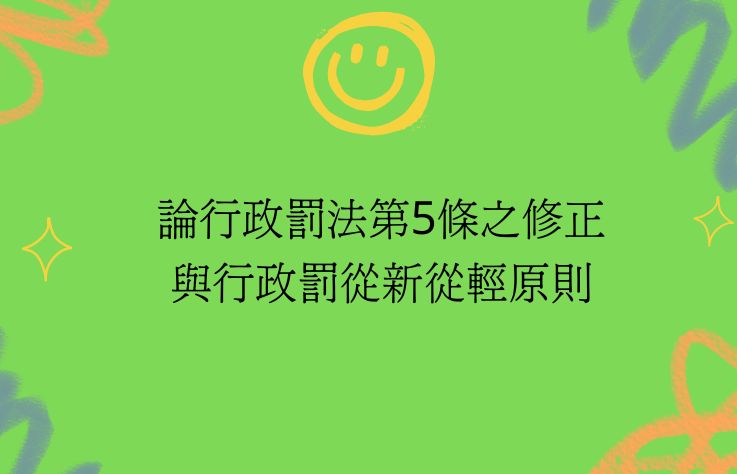壹、經典案例
被告甲為A女之父親,某日A女於家中浴室內泡澡時,甲敲門詢問是否得進入浴室幫A女搓背,一開始甲的確係以按摩砂為A搓背;未料完成背部按摩後,甲順勢將手往前至A女胸部周圍按摩,並一路順著腹部至下體,甲遂以手指進入A女之陰道內四到五秒,接著結束按摩與撫摸身體而離開。
在訴訟程序方面,A女於偵查中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80條規定告知得拒絕證言後,仍決定積極陳述,本案檢察官起訴時係以A女於偵查中訊問之供述(筆錄)作為證據證明甲犯強制性交罪。A女於第一審經傳喚到庭作證,惟當審判長告以得拒絕證言後,詢問是否願意作證,A女回答不願意後,即許可其拒絕證言;然而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並指摘第一審、第二審法院採用A女於偵查中之陳述作為證據,妨害其受憲法所保障的對質詰問權(訴訟防禦權),據以提起上訴。
貳、前言與問題意識
刑事被告對於不利證人之供述,享有對質與詰問之權利,並受憲法第16條訴訟權所保障,此為受司法院釋字第789號解釋所肯認的憲法上權利;另一方面,證人依其與被告的身分上關係或不自證己罪特權保護之前提下,得行使拒絕證言權,亦屬證人於刑事程序上的權利保障。二者間是否產生衝突而有調和之需求?刑事訴訟法(下同)於2003年修正後,增訂第181條之1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反詰問時,就主詰問所陳述有關被告本人之事項,不得拒絕證言」;由於交互詰問的制度設計本身係為檢驗證人的憑信性,以達到發現真實的程序目的,所以主詰問過程中若證人不行使拒絕證言權而為陳述,同理反詰問也不應拒絕證言;與之類似但法未明文的情形,可能發生在偵查中曾於檢察官前積極陳述,審判中經傳喚到庭後卻行使拒絕證言權,此時法院應如何取捨?禁止證人行使拒絕證言權?或是使證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即屬本題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意識。
參、實務與學說意見分析
一、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曾就第181條之1所謂「主詰問」擴張解釋為包含偵查中證人於檢察官前之陳述,不行使拒絕證言權而自由陳述者,審判中,為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權,該證人即不得再行主張拒絕證言權,以避免形成無效的反詰問。擴張解釋的前提在於:偵查、審判屬於一整體的詰問程序,偵查中不利證人於檢察官面前所為陳述,通常無法立即接受被告之對質詰問,須待審判中經傳喚到庭證述,始得對之對質詰問,補足先前偵查程序之反對詰問權利。因此,若起訴後檢察官援引不利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者,程序上相當於「主詰問」;再者,若將不利證人之積極陳述作為證據,審判中該證人必須就陳述之內容受反對詰問,與條文所述「有關被告本人之事項」無異,因此可以直接適用第181條之1規定,該證人不得拒絕證言。
晚近(十年後)最高法院再度重申,證人曾於偵查中向檢察官陳述者,於審判中不得行使拒絕證言權,不過理由改變為「類推適用」第181條之1規定,就第181條之1所為主詰問、反詰問之解釋,不再認為屬於「同一詰問程序」,而係「整體詰問程序之續行」,因此不符合法條預設文義範圍,改採類推適用見解,不過殊途同歸,最終結論都是「不得行使拒絕證言權」。
二、學說意見
上述案例中,證人的拒絕證言權以及被告的對質詰問權,同樣均屬憲法上重要的基本權利,而且二者均非不得限制的權利,因此也沒有優劣順位之區別,端視立法者於二者衝突時,以規範來決定二者的先後順序。本案第一審法院於傳喚被害人A到庭後,應就其先前於檢察官前之訊問內容,適時讓A接受交互詰問,以確保被告之對質詰問權,此一前提不變。不過另一方面,證人的拒絕證言權應如何確保?若不得已必須使用該證人於偵查中之訊問供述作為證據,那麼可能的選項有:(1) 不得行使拒絕證言、強令證人陳述;以及(2) 以傳聞法則與例外肯定或否定該供述之證據能力。第(1)種解決方案即為上述實務見解的作法,於此不贅。第(2)種解決方案,必須倚賴傳聞法則之例外作為判斷標準。首先,審判外檢察官前之陳述,依據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有證據能力,再加上釋字第789號解釋的補償衡平法則,雖有證據能力,必須要加上其他補強證據作為佐證,始得採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基礎,但這樣的作法仍可能會使該證人先前的偵訊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證據使用,如此一來,首先被告之對質詰問權是否實際受補償仍有疑問(於此不贅),再來是證人先前陳述仍被採用,無異於審判中拒絕證言是無用的,採取這種做法的結果很可能導致雙方權利皆未獲滿足。
第(2)種解決方案還有其他思考途徑:例如刑訴法第159條之3規定,雖然此一規定適用範圍是在司法警察前所為之陳述,不過考量其規範目的,其中第4款規定「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者」,例如證人於警詢時積極陳述,但後續於審判中行使拒絕證言權,依照反面解釋來思考,此時不構成傳聞例外,一來法院不得使用該審判外陳述,確保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不會受侵害;二來法院不能強令證人行使或不行使拒絕證言權,權利之行使與否仍交由證人決定。相同情況,若證人是在檢察官前為陳述者,就沒有類似規範得加以適用,惟此時證人拒絕證言權以及被告之訴訟權均有保護必要,立法者在此作出了拒絕證言權與對質詰問權衝突如何調和之決定;是以,這種情況即為違反規範計畫的法律漏洞,學者主張可以類推適用第159條之3第4款之規定。
肆、給考生的叮嚀-代結語
固然實務見解在本題的問題意識下,始終採取直接或類推適用第181條之1規定,最後結論都是讓證人「不得行拒絕證言權」,惟這樣的作法可能造成「雙輸」的局面,第一是證人陷於因特定身分關係下作證之衝突,或是因不自證己罪保護所造成的兩難困境,因而不得不為陳述;第二是被告可能因此被迫接受未經詰問的審判外陳述作為證據,喪失其對質詰問權。因此可能比較適宜的作法會是類推適用第159條之3規定,在面對這樣的題型時,首先應點出實務見解的雙輸困境,再來應該要回到法學方法上論述,證立此時存在一個違反規範計畫之法律漏洞(詳參上文參、二),才會是比較完整的作答。
~~~~~~~~~~~~~~~~~~~~~~~~~~
1.事實摘自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侵訴字第109號刑事(下同)判決。
2.此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號判決之程序事實。
3.參閱林俊益,〈無效反詰問法理之援用-你敢說不利我的話,竟不讓我反詰問,公平嗎?〉,《月旦法學教室》,第139期,2014年4月,頁30-32。
4.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668號判決參照。
5.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204號判決參照。
6.參閱薛智仁,〈拒絕證言權與對質詰問權之衝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號刑事判決〉,《台灣法律人》,第21期,2023年3月,頁144。
7.薛智仁,同前註,頁15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