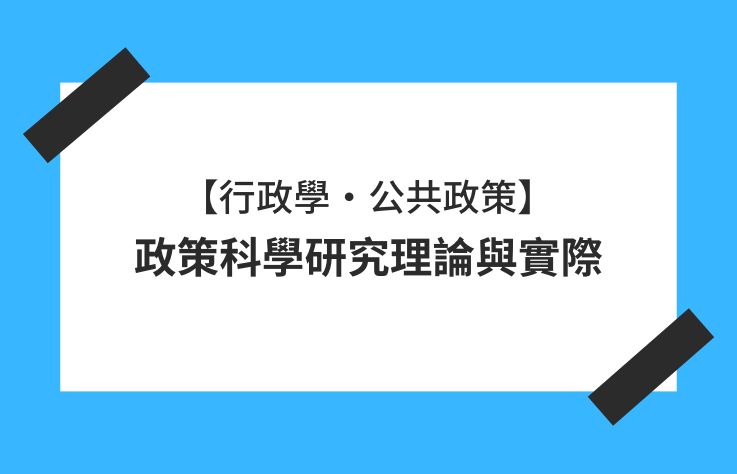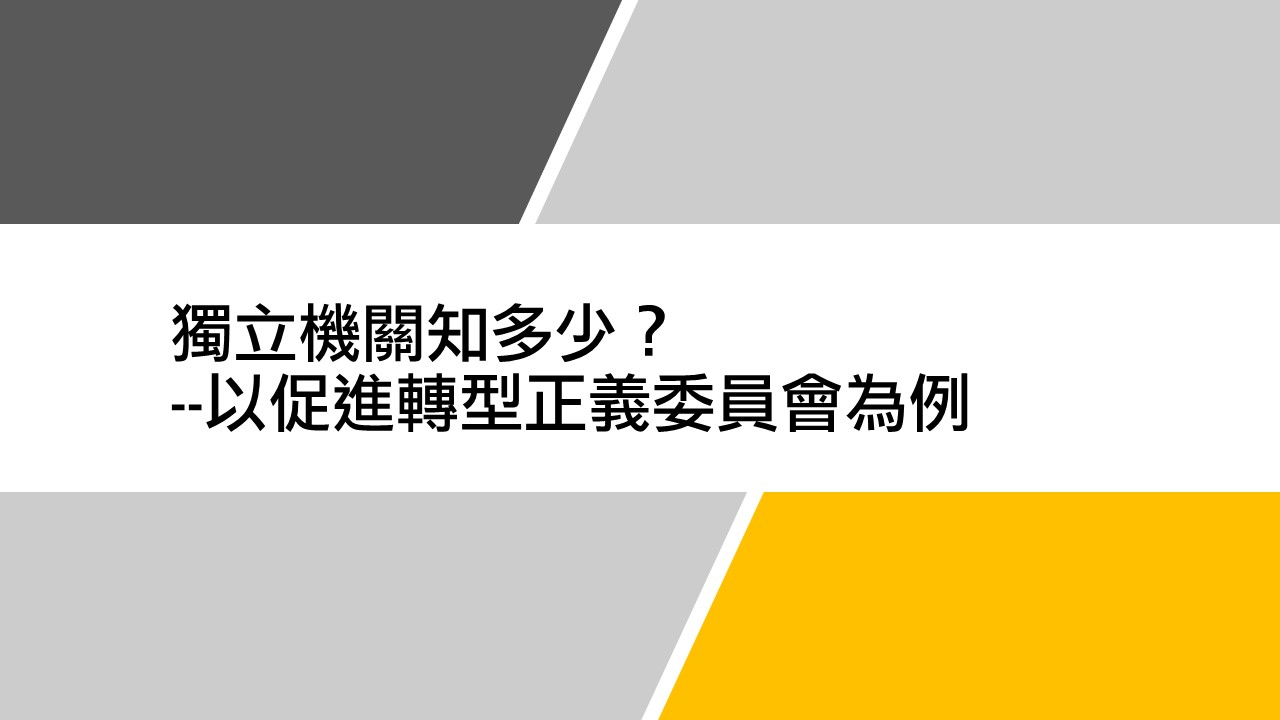政策科學的發展,可以由拉斯威爾發表《政策科學》一書作為分界,在《政策科學》問世之前,可稱之「前政策科學運動時期」(Pre-policy Sciences Movement),在此一階段,政策研究在哲學與社會科學界的思想源由與脈動雖與日後的政策科學不同,但對於瞭解日後政策科學的發展仍有俾益。至於起源於一九六○年代前後的政策科學運動,參與政策科學運動的建立者,不僅橫跨不同的學科領域,也容納了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於政策研究及分析感興趣的人士。政策科學之急,在於創建一門實用性,行動取向的社會科學,也是參與社會改革運動者在一九六○、七○年代所發起的自我批判。在經歷了不同時期的發展,原先以經濟理性/理性選擇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信心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多元途徑,尋求在不同的行為者之間創造最大共識。因此,政策過程推展的過程所累積的知識,以及政策過程中不同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即成為當前政策科學主要研究焦點。隨著參與式民主對於國家中心決策模式的挑戰,政策科學亦應早作因應,以期深化民主政治的發展。
壹、前言
政策科學在技術上屬於專家主導,科學至上的一門學問。然在實務應用上,由於公共問題的層出不窮,科技發展不僅展現造福人群的潛力,也提高了社會生活的各種風險。因此,政策科學的民主意涵,引起有識者的關注。政策科學與政策專家的角色逐漸由主導者轉變為輔導者,進一步朝向建議者的方向發展。在民主深化的過程中,公民參與所強調的偏好的表達與彙整,與政策科學所強調的理性分析程序之間的對立逐漸尖銳化。易言之,民主與專業之間如何調和,成為民主政治能否由量的計算,提昇至質的改善的關鍵因素。
政策科學自1960年代以來,已經逐漸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實務與學術領域。但是政策分析在實務與理論的角度來看,仍然屬於政治大環境的一環,各種的直接民主參與形式,創造「電子賦能」(E-enabling)、「電子賦權」(E-empowerment)、「電子交往」(E-engaging)等模式,使公民參與已經逐漸被視為現代治理的重要基礎。因此,民主的政策科學因應當前的民主思潮,亦需面臨重大挑戰。以下,謹就政策科學的概念進行釐清,再議政策科學的發展、面臨的挑戰,最後耙梳政策科學當前可以扮演的回應。
貳、政策科學的定義與概念
政策科學的概念,最早於1951年由拉斯威爾及雷納(Lasswell and Lerner, 1951)所發表的《政策科學》(The Policy Science)一書所用,在這本書的第一章中,拉斯威爾說明了政治學的研究,必須著重於「政策取向」(Policy Orientation)的發展,以強化政治學對於實際政治以及政府運作的影響,透過政策過程與政策內容兩個面向來討論美國社會問題,將有助政治學正當性的強化。拉斯威爾的見解被視為政策科學運動(Policy Science Movement)的序幕,之後,眾多優秀學者追隨拉斯威爾的見解,持續貢獻,終於使得政策科學的發展蔚然成風。
必須注意的是政策科學的發展並不像預期般的一帆風順,倘若從孔恩(Thomas Kuhn)所提的典範(Paradigm)觀而言,難以明確地描寫出政治科學發展的清楚脈絡。有學者認為,檢視當代政策科學,會發現兩種不同典範,一種是重視技術、強調經濟理性的管理觀點;另一種則為追求理論、重視政治脈絡的政策觀點。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科學之分類並不止於此,有學者檢查著名政策期刊中有關政策科學的研究著作,他們發現政策研究和分析領域中,幾乎無法找到公認的科學典範,即使大體上可以分為量化的經驗研究和非量化的論述型研究(Schneider et al., 1982)。
丘昌泰(1995:3)認為從典範的發展型態來說,政策科學典範可以區分為兩大流派,一種是傳統的政策科學典範,另一則是當代的政策科學典範。傳統的政策科學典範認為政策科學必須展現明顯的「科學性」才能被承認為專業學科,因此,政策科學必須建構一門以量化研究途徑為核心的學術研究,並且透過專業化的標準,來確保政策研究的成果與品質。而傳統政策科學典範,也因此在方法論上傾向邏輯實證論,以經濟/工具理性(Economic /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作為推論基礎,主張透過量化來作為分析的工具;並且透過作業研究、系統研究等技術性的管理決策工具來突顯政策的問題結構、政策過程、政策規劃、政策執行、政策評估等面向。
而當代的政策科學則認為政策科學並非單純的科學,而是兼容更多變數的藝術。因為政策科學家面對的問題過於複雜,透過科學方法與程序所獲致的資料極為粗糙,不但無法適當的描繪決策者內心世界,其信度與效度更不必然可靠。更重要的是非理性資訊的量化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丘昌泰,1995),公眾輿論、報章媒體、個人偏好等面向在分析中常常被忽略不計。因此,當代政策科學的立場,主張必須採取後實證主義的立場(Post-positivism),以社會理性或實質理性為基礎,強調質化,更為精細的分析公共政策決策個別面向。
整體而言,丘昌泰(1995:11-18)主張政策科學具有三大特質:
一、多元學科的研究途徑
拉斯威爾主張政策科學是科際整合的縮影,也就是政策科學的目的在於整合各種學科的研究與理論,彌補單一學科途徑可能造成的問題與盲點。據此,政策科學在發展初期,展現了兼容並蓄的特性,舉凡權力結構、精英理論、團體理論、人事、預算、組織均是政策科學的重要分析與課題。然而,由於此一階段的政策科學欠缺統一性的經驗理論,無法進行學科對話,門戶之見益深、主要的研究問題亦乏大量的個案累積,在知識上尚不足以進行整合與合作,因此,有學者認為政策科學實際上並無法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至多僅是啟蒙決策者的政治認知,並不能對實際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但實際上,政策科學家亦不必過於悲觀。因為公共問題實在過於複雜,單一學科並不足以解決問題。多元學科的科際整合也不意味著政策科學研究者或政策制定者必須要全知全能,反而具有解決公共問題的精神與態度更為重要。再加上不少政策科學家已經開始從事政策知識的科際整合,兼容國際化勢,納入更為複雜的問題,政策科學的開展仍有一定可能。
二、問題取向與系絡特性
政策科學在本質上都是問題取向的,其所關懷者,即是當代社會中人類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包括貧窮、社會福利、分配正義等。這些問題的內容都極為複雜,不同的政策目標彼此產生衝突、政策行為者之間經常互動、政策問題彼此相互關聯、政策決策過程的資訊並不完全此策科學的發展上必須更為廣泛的採取不同的社會科學方法,才能適當的提出解決方案。由這角度上,又可區分三大面向。
(一)政策內容:
政策內容的研究者,擅長以計量模型來解決實務問題,多數屬於作業研究者或凱因斯學派的經濟學家,特別重視政策的分析與政策技術的運用。他們相信最佳解決方案的存在,更主張政策科學與作業研究是同義詞,而認定目標、研擬方案、評估影響、決定標準與選擇模式就是政策分析要因素。
(二)政策過程:
政策研究者也極為重視政治與組織過程的知識,因此他們不認同計量研究者篤信的全稱理性(認為理性可以解釋一切現象的主張),反而主張多元政策觀點,強調體現真實世界的決策過程之重要。因此,決策過程中,缺乏共識、沒有標準,論述過程常常左右了最終政策,但整體而言,非理性的決策模式極為常見。在政策推進的過程中,妥協、漸進主義與不斷調適反而比較接近現實。
(三)外顯規範觀點:
拉斯威爾曾指出政策科學的研究途徑之前提,必須對於政策所涉及的價值及目標有所釐清。政策科學成立的目的並不在加強效率的提升,而是在於人類尊嚴與能力的實現。因此政策科學家在政策制度過程中應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社會正式價值的確立,回應社會價值的需求。主因在於政策分析本身即是承載價值的存在,價值本身即是目的,也即是利益所在。因此,政策科學家自身決非中立,在揀選研究方法時,即已決定價值的判斷。因為政策制度是在相互競爭的價值觀中進行一場沒有結束的爭鬥,公共政策的制度是價值判斷的工作。因此,拉斯威爾倡議「民主政策科學」(The Policy Science of Democracy),以取代傳統具有威權傾向社會科學研究。他主張新的政策科學發展必須一方面運用社會科學的調查方法,一方面納入更多的價值詮釋,兩方面齊頭並進才能在政策科學的發展上建立正當性。
邱昌泰認為政策科學自創立以來,就曾遭到三種挑戰:漸進主義者(Incrementalists)的挑戰,過於強調政策過程中,政治因素的影響力,將政策窄化為政治利益的犧牲品,政治理念可以透過協商或交易得到妥協;過於技術取向的量化研究者,因為對於價值中立的錯誤認知而不敢悍衛民主價值;過於重視科學性,誤認政策科學家應該避談價值問題。但事實上,完全價值中立或是認為計量研究足以解決規範性價值問題忽略了政策制定過程中,實質上正是不同的價值觀持續的爭鬥,倘若公共政策研究不納入價值理念的研究,其範圍將會顯得過於狹隘,更無法突顯公共政策屬於價值判斷的本質。如同拉斯威爾強調「民主政策科學」(The Policy Science of Democracy),即使是以計量研究與心理學見長的拉斯威爾,亦強烈主張政策科學除了實用功能的提升以外,必需有更高遠的學科發展目標,以及提供實現人類尊嚴與價值的知識,而這正是民主政治的能力。因此,民主政策科學之精義,正是推進民主政治之發展。拉斯威爾特別強調民主政體面對寡頭政治與官僚主義所具有能力,倘若民主政治流於少數政治精英與技術官僚的專業意見,則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公民秩序將蕩然無存,民主國家也將淪為「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屆時政策分析家將成為政府的奴僕,失去了政策科學發展的最高價值。
參、政策科學的發展
政策科學的發展,可以由拉斯威爾發表《政策科學》一書作為分界,在《政策科學》問世之前,可稱之「前政策科學運動時期」(Pre-policy Sciences Movement),在此一階段,政策研究在哲學與社會科學界的思想源由與脈動雖與日後的政策科學不同,但對於瞭解日後政策科學的發展仍有俾益。至於起源於一九六○年代前後的政策科學運動,參與政策科學運動的建立者,不僅橫跨不同的學科領域,也容納了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於政策研究及分析感興趣的人士。政策科學之急,在於創建一門實用性,行動取向的社會科學,也是參與社會改革運動者在一九六○、七○年代所發起的自我批判。
政策科學運動興起的主因在於詹森總統任內,發動諸多重大工程,包括了大社會計畫,投入大量的經費與人力,但成效令人失望。失敗的原因,包括了社會計畫的制度與執行過程中,過度倚賴社會科學知識,但該時的社會科學方法並不夠精確,並且社會科學的發展仍有明顯侷限。因此,社會科學的權威性明顯式微,社會科學理論避談價值,不夠廣博,缺乏解決方案,都使得政策科學另尋研究益形必要。此外,由於一九六○年代多數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為行政與立法部門所建立,普遍而言,這些研究就在於服務當權派,但事實上,諸多社會問題缺乏明確的價值與定義多不同的行動團體彼此之間缺乏共識。因此也連帶影響政策制定者的權威性。自此,政策科學家發起一連串的政策科學運動(丘昌泰,1995)。
一、一九五○至六○年代的萌芽時期
拉斯威爾的《政策科學》一書,揭開了政策科學運動的發展,拉斯威爾對於戰後的社會科學離心力量的盛行感到不滿,他認為必須跨越分離的專業領域,建立統合的社會科學。政策科學的早期發展中,以經濟學家為主要的參與者。在聯邦政府中,就有3,000名以上經濟分析師遍布的不同的部門。政策科學運動早期的研究重點,在於國會與聯邦政府負責制定與實施的立法政策。特別是甘迺迪總統任內通過多項法案,包括《民權法》、《中小學教育法》、《經濟機會法》、《公車犯罪管制與安全街道法》,這些法案都是經過學者專家再三的審議以期發揮積極功能。該時由於第三代電腦開始發展,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興趣大為增加,技術性的分析大為推展,包括作業研究、系統分析、線性規畫均使得政策科學在以效率為核心的概念上積極推展。
但此一時期政策分析家普遍具有的樂觀信念,忽略了設計與預算運作不成功的弊病,被批評是計畫完美,績效有限;再加上此一時期的政策分析家普遍認為分析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態度流於天真,在實際的執行上招來嚴重批評。
二、一九七○至八○年代蛻變時期
此一時期的公共政策,已經明確認知到理論與實際上的困難,在研究方法上必須進行修正。在此一時期,出現了三方面的特徵。
(一)政策科學社群的自我檢討:
一九六○年代,聯邦政府推動許多重大公共政策,在社會學與心理學家的參與下,政策評估的重要性受到重視。一九七○年代,美國聯邦政府機關約有三百多件政策評估的研究案,總經費約達三千萬美元(丘昌泰,1995)。流風所及,政策科學應創造能夠結合實際經驗與科學方法的政策知識顯得更為必要。另外,政策執行過程的政治與官僚對於政策的成敗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再好的政策,倘若缺乏好的執行者,仍然會導致政策的失敗。最後,到了一九七○年代能源危機出現以後,政策科學家開始嚴肅思考中止失敗政策的必要。「小政府」成為此時期逐漸興起的意識形態,政策科學家提出縮減管理的觀念,希望透過削弱政府的職能、減少不必要的冗員,降低政府的赤字預算,以期降低政府不必要的支出。
(二)實務社群的重大政治與社會事件的衝擊:
在現實世界中,有幾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影響政策科學對於現實政策形成的認知(丘昌泰,1995)。
1.反貧窮戰爭:
為了向貧窮宣戰,詹森總統積極推動了許多社會福利計畫,包括教育、住宅、營養與就業計畫,這些計畫的結果令人失望,但是反貧窮戰爭,確實讓政策科學家從政府與民間那邊得到大量的財務支援,促成政策研究的興起,同時也拓展了政策科學家對於社會問題複雜程度的瞭解。
2.越戰:
越戰對於政策科學的影響顯著,著名的藍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空軍及國防部長辦公室建議之下,發展系統分析與成本估計技術,建立以政策為導向的國防經濟學(丘昌泰,1995)。此外,美軍對抗越共的經驗顯示理性分析模型難以適用於越南戰場,反而漸進主義的模式逐漸受到重視。
3.水門案:
水門案對於政策科學的影響是道德標準的重要性提高,政策科學家也同意沒有正當的道德指標為核心,再精緻的公共政策將無法緩解人民心中的苦痛。
4.能源危機:
一九七三年與一九七八年的兩次石油危機,除了促使學術界以數學模式去建立能源供需模型。有鑑於石油公司形象不佳,社會民眾的不信任感大幅提高。不少民眾認為石油公司是謀取暴利的巨靈,政策分析家對於政府及人民之間的對立情形,必須要有更多的瞭解。
(二)政策研究取向的改變:
由於受到政策科學社群中的自我批判,實務社群受到重大政治社會案件的影響,政策科學家發現政策研究並非萬靈丹,只能促成政策的形成,不能取代政策的決定。在這種背景下,政策科學家的主要任務不再是找出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最佳方案,而是在交互關聯的利害關係人之中取得共識。因此,政策科學不能客觀地脫離決策者與利害關係團體的價值體系,而是必須融入於政策過程當中。基本上,此一時期政策科學家對於政策研究的看法,走向限制觀,認清政策的侷限(丘昌泰,1995)。
三、一九九○年代以後的多元時期
當代的政策科學發展開始去修正舊有的研究主題,並且持續開拓新的研究方向。主要發展有三,分別是(1)舊研究主題的修正、(2)新研究方向之定位,以及(3)政策科學的建制化。
(一)舊研究主題之修正:
主要是重申公共政策倫理與價值研究的重要性,自政策科學運動興起以來,從未正式承認過倫理與價值之重要性,因為政策科學是以理性選擇理論為基礎,政策問題需要選擇、政策目標需要選擇、政策方案更需要選擇。但自從一九八○年代以來,羅爾斯(Rawls)的正義論就強調以功利主義為主體的倫理應該被分配正義所取代(丘昌泰,1995)。而倫理問題與社會道德的重要性再起,從國家安全、社會福利、死刑等倫理問題,一再顯著公共權利議題需要更多的關注。因此,專業與行政倫理重要性提高,必須要融合管理與組織行為、政治與政策形成理論,才能有效地管理公共政策。
(二)新研究方向之定位:
隨著社會問題日趨糾葛難解,新的社會問題對於公共政策研究者構成相當大的挑戰;以實證論為主體的客觀研究方法已經不能發揮效用,後實證論為主體的主觀研究法,開始重視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價值與倫理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經濟與技術理性為主體的理性選擇論強調的「利益最大、損失最小」,同時也重視政策制定者對於政策具有的偏好優先順序並無法對於政策做出適當評估與選擇。相對地,以社會、政治與法律理性為主體的政策調查逐漸興起(丘昌泰,1995)。政策調查者認為沒有最佳政策,可以能夠為全體社會大眾所接納。什麼是好的政策?則必須由理性意識形態的政體所決定,透過政策辯論所得到的合理性(Reason)來決定是否接受某項政策前提條件。
(三)政策科學的建制化:
公共政策研究發展迄今,已經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從學術社群的建制化而言,愈來愈多美國大學校園內,成立獨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所,包括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匹茲堡大學、耶魯大學。公共政策學會相繼成立,公共政策期刊蓬勃發展,而實務社群的民間智庫也相繼成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史丹佛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對於公共部門、聯邦、州、地方政府的決策影響力正逐漸增加。公共政策的建制化反映政策科學卓然有成。
肆、政策科學面臨的挑戰
在經歷了不同時期的發展,原先以經濟理性/理性選擇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信心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多元途徑,尋求在不同的行為者之間創造最大共識。因此,政策過程中所產生的知識已成為政策科學分析中的重要任務,這些知識包含經濟、社會、科技等領域,政策過程不同行為者之間的互動乃成為政策科學領域中的重要特徵。就政策過程推展的過程,主要的討論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基於「政策過程發展」所累積的知識,包括了議程設置、政策制度、政策執行、政策評價、政策決策等不同階段,此為當前政策科學分析主要焦點。另一個方向則著重於「政策過程中不同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了不同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政府、政客、官僚、利益集團、社會組織、專業人士與相對的組織團體等利益相關人在不同層次之間的互動與競爭過程,此為多元主義分析的核心所在。政策網路的分析框架雖然有助於我們瞭解政策過程產生的互動,但在實務與理論研究上仍然存在一定落差。
根據丘昌泰(丘昌泰,1991)的見解,有鑑於政策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較預測更為複雜,甚至常在政策過程發生之後才會出現。而複雜世界的因果關係模式亦難以描繪多元關係的政策現實。再加上政策存在的複雜性,再再說明採取多元的研究方法,保持彈性,在進行政策分析上更為重要。
在台灣自1990年代的民主化與民主深化的過程中,由於公民政治參與的提高,民主決策的民主化以及政府角色的調整,公共政策的複雜性超過以前,在公民治理的時代,當前政府治理的挑戰,已不再是如何達成管理的效率,而是如何實現草根民眾之所欲。新世紀的官僚走向小而美、績效導向的趨勢下,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公共行政領域出現了兩種主要的發展,首先,強調公民參與的政府再造與公民治理受到重視;其次,政府績效評量與管理受到強調。因此,當前的公共行政學界正企圖結合此兩者,以有效提升政府治理與公共服務的品質。
從政策科學的角度而言,重視參與民主的政策科學正逐漸興起。究其因,乃在於「正當性」(Legitimacy)概念的興起。過往重視經濟與技術理性做為政策制度方案思考主軸的政策科學,忽略民主參與政策科學的重要性,忽視公平與正義的民主價值,在民主時代,往往造成社會認知與政策執行的落差,事實上,以民主政策的方法所建立的參與民主政治中,既不否認衝突的無可避免,又兼顧民眾、專家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以追求民主共識的過程。易言之,公民參與應成為地方治理的核心議題,特別在涉及地方居民利益之議題,納入地方民眾解決爭議的重要性逐漸提高,建立鼓勵公民參與,兼顧民主實踐的政策科學,亦為回應民主發展的重要趨向。
由這點而言,政策科學受到參與民主的影響,如果欲取得更高的正當性,則如許立一(2004)所言,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大為提升:
一、公民主動參與的精神受到重視
因為人民意識到自身做為社群成員的集體性,激發了作為成員的身分認同,因此強化了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對於透過行動改變社會價值觀的態度更為強化。
二、政策知識的共享
公民參與政策的目標在於提升社會,人們在其社群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政治的行動和學術對於參與民主的反省,將使政策科學與相關知識有更高的公共性,並且在積極的社會之中,公眾應該被視為政策分析者的一分子而不是被排除在外,知識菁英應該與公眾針對集體課題展開互動。
三、理性的公共辯論
作為社群成員的民眾可以透過公共討論的轉化過程來調解差異,尋求共同的價值與利益基礎,進行建立解決問題的最大公約數,強化問題解決方案的合法性。由上所述,公民參與之概念具備多樣性,從不同領域切入有不同的意義,其核心價值仍圍繞在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公民表達意見的權力、公民主權的認知與改變、公民公平公開的參與管道、落實民主政治、追求最佳公共利益之目標。
當前,政策科學仍有三大挑戰尚須克服。分別是「民主與專業之矛盾」、「代理人成本與其限制」、以及「公民參與的多樣性」(郭耀昌,2012)。
一、民主與專業之矛盾
民主的發展,是廿一世紀政策科學最大的變局,主要的原因,在於公民在政治上的參與,與傳統的政治參與遠遠不同。傳統的政治參與,亦即代議式民主,人民選出代議士之後,即賦予代議士對於所有的政治議題進行協商並且制訂決策的權力。在此一脈絡下,傳統的代議政治基本邏輯,乃是建築於人民低度的政治效能感,由於政治參與具有高度的門檻,必須具有足夠的專業、資源與管道才能介入,因此一般民眾在參與成本過高的情形下,代議政治自然是較佳的解決方案。然而,晚近20年的資訊科技革命、新媒體的發展、影音匯流的擴張,公民取得政治與社會議題的資訊與傳統政治大異其趣。以往官僚主義剝奪了人民直接參政權利的正當性受到高度挑戰。
由於網路興起,公民在歷史上首次取得直接介入公共決策的可能性。美國總統歐巴馬利用網路動員而獲得的歷史性當選,更激起全球各地風起雲湧的青年革命。倘若近年來一連串的公民參與代表人民已逐漸能夠透過網路積蓄民意,並且轉化為實際的行動影響公共利益,在這個脈絡下,當今公共管理者、政策科學家都必須在政策管理的領域,反省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重構更符合當今現實的知識。
二、代理人成本與其限制
由於距離、知識的差距,民主政治迄今仍需仰賴代議制度的運作。根據Arnstein根據公民對於於公共決策所能發揮的影響力,建構出公民參與的8個層次(李柏諭、劉鴻陞、陳柏霖,2012:58):
(一)操縱式參與:
民眾在參與過程中處於被政府教育的地方。
(二)補救式參與:
民眾參與的過程是用來彌補政府決策挫敗的工具。
(三)公告式參與:
民眾在參與過程中,被動得知政策決策規畫後的結果。
(四)諮詢式參與:
民眾在參與過程中可以表達意見,但無法保證民眾意見會被納入決策規畫之中。
(五)安撫式參與:
民眾在參與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並不足以影響最後決策。
(六)夥伴式合作參與:
民眾在參與過程中與政府處於對等地位,以合作互信的方式共同規畫決策。
(七)委任式參與:
民眾在參與過程中擁有充分的規畫決策能力,政府僅處於監督與支援的角色。
(八)公民控制式參與:
民眾在參與過程中完全掌握與主導決策規畫,並對決策的結果負責。
以上8種形式的公民參與顯示了人民對於政策決定過程中的影響力,而在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中,公民參與的程度逐漸提升,也因此使得公民參與具備意見反饋的重要功能。由Arnstein的說法,可知道公民參與的最終目標固然在決策上,但決策可分為技術官僚的決策(Technocratic Decision-making)與民主的決策(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前者涉及專業事務,多由技術官僚為之;後者則係一般公共事務,利害關係人不僅具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其意見更應該尊重(紀俊臣,2015:21)。當前,由於議會制度陷入危機,大眾民主的發展已使公開辯論變成空洞的形式,各利益團體動員宣傳部門爭取群眾,以合理化自身利益的爭取。在威權時期,政策網路的管理,乃由國家機關所專擅,由於國家是社會秩序的唯一主宰,因此以主導的政策網路的訊息流動與規範,但這種以國家為本位的管理方式,自然對於社會的發展造成壓迫,進而削弱國家機關的合法性。流風所及過往以官僚為核心所建構的「統治」機制,也由強調公民參與的「治理」代之,為了重塑國家的正當性,由國家與社會共治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業已成為國家機關所接受。易言之,在新的治理模式中,公部門、私部門與公民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已經成為當代最重要的治理模式。
三、公民參與的多樣性
當前民主政治對於公民參與仍有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之別,如果再考量到全球化改變了國家與社會的組成關係,國家的部分權力逐漸向上流動,與國家逐漸將行政權及財政權下放擴大地區的自主權力的情形同時發生。在這種國家權力向上及向下流動的雙重趨勢之中,草根公民參與政治對於決策的影響愈來愈大,因此科技決策的相關領域,舉凡地區發展規畫、能源計畫、國土規畫等由專業領域,亦應思考倚靠中央政府單方面決策的模式,是否應予修正,容納公民參與的意見。一般而言,一般民主國家的公民參與主要有三個部分(鄭得興,2013):傳統的政治參與(選舉投票)、公民團體的參與(非政府組織NGOs、非營利組織NPOs與第三部門)、及其他政治或社會行動的參與(遊行、集會、募款、扺制、線上論壇)。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中,公民參與多數超越傳統的政治參與,趨向公民團體與社會行動方式的參與,因此造成政治體制的轉變。
在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中,公民參與常被視為推翻威權體制的關鍵,特別在民主轉型過程與民主鞏固過程中,建構健全的公民社會甚為重要。因此,Hurlbert & Gupta主張分裂階梯參與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整合了Arnstein的階梯理論,另外提出了3項:(一)診斷、(二)評估、(三)策略三項工具去處理政策問題(林美秀,2018)。
(一)診斷工具
乃是以信任因素、價值、不確定為基礎去判斷何時參與能夠成功,此一階段的資訊多半充滿了高度不確定性,同時參與政策的利害關係人並無法立即達成共識,對於評估什麼程度的參與亦有高度困難。
(二)評估工具
在這情形下,參與者將依據過往的場所、脈絡、時機以及問題的本質等因素,來考量參與的技巧以及理解政策的脈絡。
(三)策略性工具
政策制定者對於政策的瞭解,以及對於公共參與的認知,建構了政策學習與公共參與的價值。
紀俊臣(2015:22)亦認曾指出評估公民參與的有效性,公民參與在原則上應符合法定條件;明定使命和目標;獲得政治支持;整合決策結構;了解事涉或影響的群眾;規範參與人的清楚角色和責任。由此而言,除了參與的階段性過程,適當的評估實為當前參與民主成功的關鍵。
伍、結論:民主政治與政策科學
根據魏陌、陳敦源、郭昱瑩(2001)的研究,二十一世紀對於民主國家而言,充滿了挑戰與希望。民主的改革並不會因為二十世紀全球化的急速擴張而減緩。未來,政策科學應扮演三大角色。
一、政策科學必須因應代議制度的發展
瞭解到政治人物利用資訊不對稱而謀取自身利益的情形,瞭解到政府決策的優先順序、利益分配與政策過程等實際情形,儘可能強化決策透明度,以避免隱藏利益為既得利益者所得的情形。
二、政策科學應從專業為弱勢者發聲
政策科學應將利益分配的平等視為政策科學的重要目標,以協助無法發聲的利益相關者之利益可以得到保障。特別是政策執行往往創造「沉默的犧牲者」,包括缺乏專業知識而受損,或是尚未出生的下一代,政策科學可以透過資訊的揭露與宣傳,維持社會公義。
三、政策科學可以深化民主
透過對於公部門的政策分析與宣傳專業倫理,可以使得社會大眾更為理解其權益之行使,以利政策正當性的形成,社會福祉的到達。
有鑑於公共政策已由國家中心主義導向公民社會中心主義,加以公民社會創造力、資源與動員能力的增加,政策科學亦應調整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以期創造更為健全的民主體制。
~~~~~~~~~~~~~~~~~~~~~~~~~~~~~~~~~~~~
Lasswell, H. D., 1951.“The Policy Orientation,”in Lerner and Lasswell eds., Policy Scienc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蔡岳勳、王齊庭,2014,〈以彈性公民多元參與模式促進綠色能源發展之法規政策初探〉,《法治與公共治理學報》,第2期,頁63-91。
丘昌泰,1995,《公共政策:黨代政策科學理論之研究》,台北:巨流。
丘昌泰,1991,〈當代公共政策中的多元主義〉,《中國行政評論》,第1卷第1期,頁81-103。
郭耀昌,2012,〈公園與及政策科學的對立與調和〉,《玄奘管理學報》,第8卷第2期,頁25-54。
林美秀,2018,《我國公民參與實踐現況初探─以台止市政府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許立一,2004,〈地方治理與公民參與的實踐:政治後現代性危機的反思與解決〉,《公共行政學報》,第10期,頁63-94。
鄭得興,2013,〈新興民主國家之公民社會及參與民主:台灣與捷克之個案研究〉,《法治與公共治理學報》,第1期,頁59-100。
李柏諭、劉鴻陞、陳柏霖,2012,〈從公民參與觀點看彰化馬興村社區炯造之歷程〉,《公共事務評論》,第13卷,第2期,頁55-75。
紀俊臣,2015,〈議會政治與公民參與:臺灣經驗的檢視與展望〉,《中國地方自治》,第68卷,第8期,頁4-27。
魏陌、陳敦源、郭昱瑩,2001,〈政策分析在民主政體當中的機會與挑戰〉,《中國行政評論》,第11卷第1期,頁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