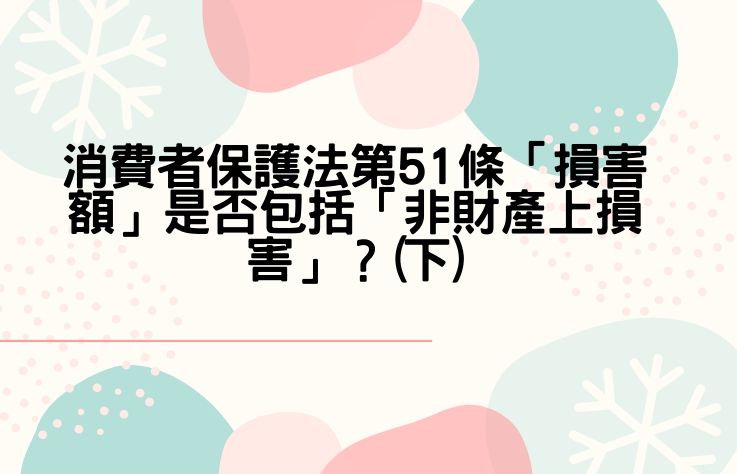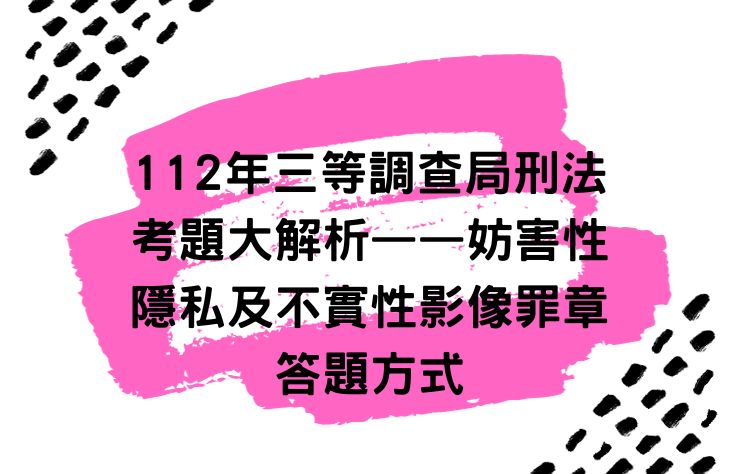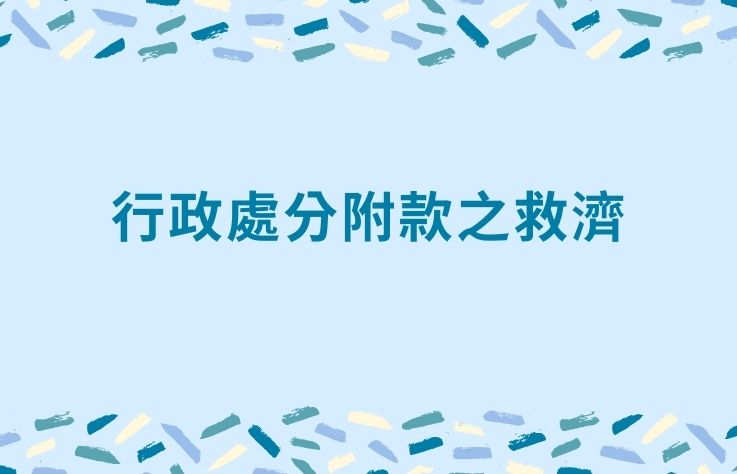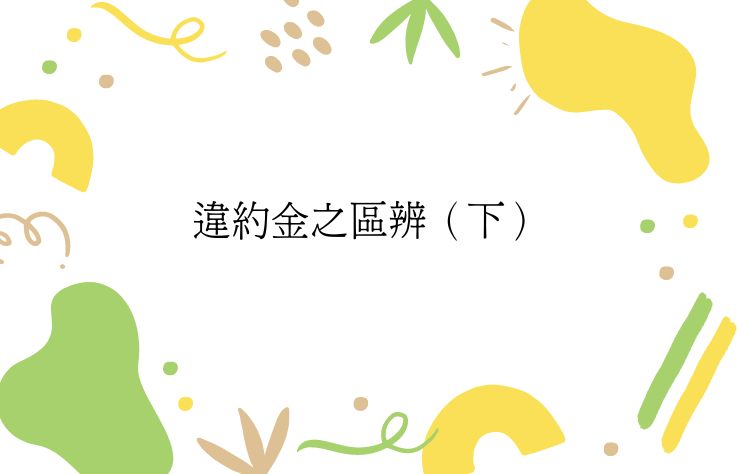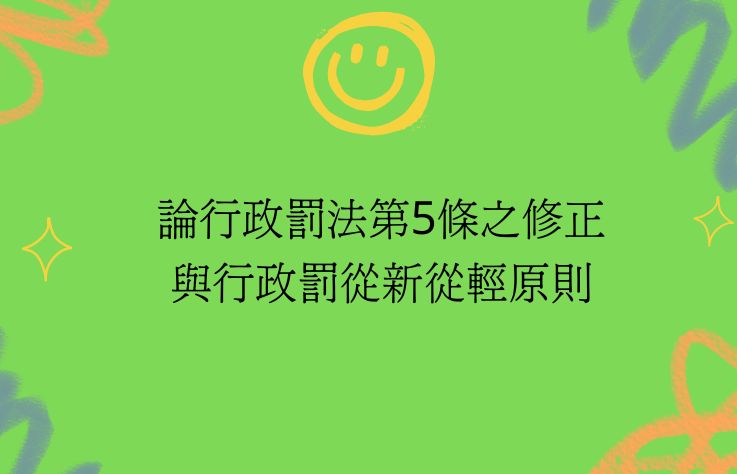延續上篇,下篇接著討論為何懲罰性賠償金應將非財產上損害納入計算
四、分析我國司法實務對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
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 是否納入消保法第51條「損害額」計算之議題,與慰撫金和懲罰性賠償金功能之差異息息相關,學者受司法院委託針對「慰撫金酌定標準與金額」進行之研究計畫期中報告書 中雖指出,最高法院有時會考量加害人於行為時的可歸責程度,作為慰撫金的參酌因素,似有意將「懲罰制裁」、「損害預防」等觀點導入慰撫金制度。
但實際法院審酌加害人可歸責程度做為慰撫金酌定之因素在案件比例上,據該研究報告數據統計結果顯示,最高法院為3.1% 、台灣高等法院為22.9% ,似尚非實務上穩定而一貫之見解,本文查詢最高法院近年 關於慰撫金酌定之考量因素,多為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犯後態度 、權利受侵害程度 、精神痛苦情狀 等,考量加害人可歸責程度之判決比例極低 ,令有於酌定慰撫金時考量加害程度者 。然本文以為依上下文此係指被害人所受侵害程度而非加害人主觀上可歸責程度,故未納入計算。
故由實務操作上看來,法院尚未有意識地將加害人之可歸責程度納入慰撫金之酌定因素中,亦即實務並無意透過慰撫金「懲罰制裁」或「嚇阻」加害人,可見慰撫金和懲罰性賠償金機能上仍有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由此亦可回應上述否定說之學者見解,蓋慰撫金既無懲罰制裁機能,將其納入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基礎並無「一行為二罰」疑慮,另本文認為,慰撫金不因納入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礎而因此染上懲罰制裁色彩,因為慰撫金此時僅是用來計算懲罰性賠償金之手段,與所計算出之懲罰性賠償金性質上仍有不同,此時毋寧須檢討的是以損害額作為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礎是否具正當性?
又在財產上之損害作為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礎時,學說卻無財產上損害因此帶有懲罰色彩而要排除於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礎之顧慮,亦未見非財產上損害與財產上損害區別之正當基礎,若欲以此做為反對慰撫金成為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礎之理由,論理上似有缺漏。
五、 附論:以「損害額」連結懲罰性賠償金計算之正當性?
消保法第51條以「損害額」作為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基礎,然因條文中未對「損害額」加以定義,導致實務上諸多爭議外,另一個值得思考之處在於以損害額連結懲罰性賠償金計算之正當性。
立法理由指出該項係參考美國、韓國之立法例,故應可推論此以損害額作為懲罰性賠償金計算基礎之方式,係受美國法強調懲罰性賠償金與填補性損害賠償間須有數額比例(ratio)的影響 ,該見解主要係為解決高額裁決之問題,然我國實務上對慰撫金之操作遠較美國保守,少有高額懲罰性賠償金之判決。且填補性損害賠償與懲罰性賠償金功能及目的本有不同,前已論述,此將兩者連結之計算方式毋寧徒增混亂與困惑,又惡性重大之侵害行為實際上可能僅造成輕微損害,消保法第51條之立法方式於該情形即無法發揮懲罰性賠償金懲罰與嚇阻的主要功能。
另有學者批評以一定實際損害比例計算懲罰性賠償金,加害人(尤其商品製造人)可透過成本利益考量計算,分散賠償金額於消費者,自經濟觀點而言,加害人實際上獲利仍高於其所負之賠償責任,無法達成懲罰性賠償金嚇阻不法行為之功能 。
六、 結論
綜上所述,觀之消保法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之設計,從文義解釋上看來無法得到立法者有意排除非財產上損害,另從目的解釋出發,為發揮懲罰性賠償金之懲罰、嚇阻目的,毋寧更應將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納入損害額一併計算懲罰性賠償金。
且由慰撫金與懲罰性賠償金之目的、性質比較可看出兩者之不同,實務既未有意識地在衡量慰撫金時考量行為人之歸責程度,則其在消保法第51條損害額認定上以避免「一事二罰」為由排除慰撫金顯屬無謂之憂慮,不應自縛手腳。
是以本文以為我國懲罰性賠償金以損害額倍數之方式計算尚有可議之處,在現行法下為避免商品製造人事先透過成本分析之方式架空懲罰性賠償金之功能,將慰撫金納入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基礎,使慰撫金難以精確估算、預測之特色於此時得以發揮,而減弱懲罰性賠償金之可預測性,不失為一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