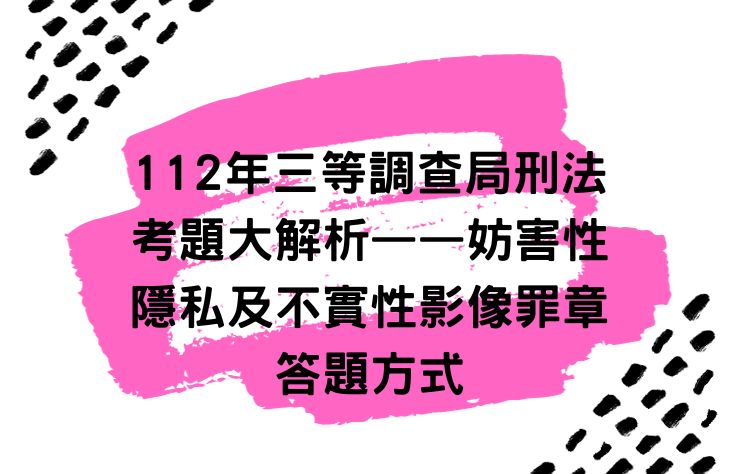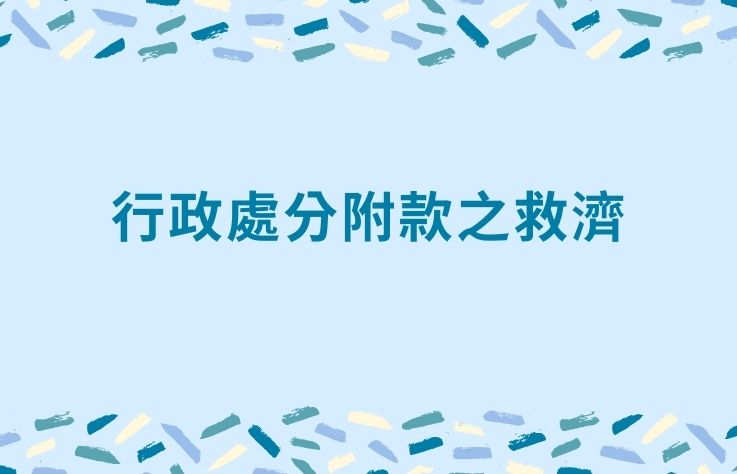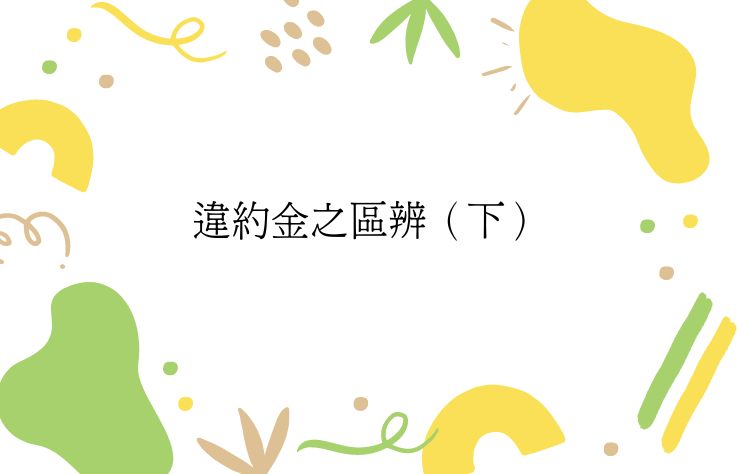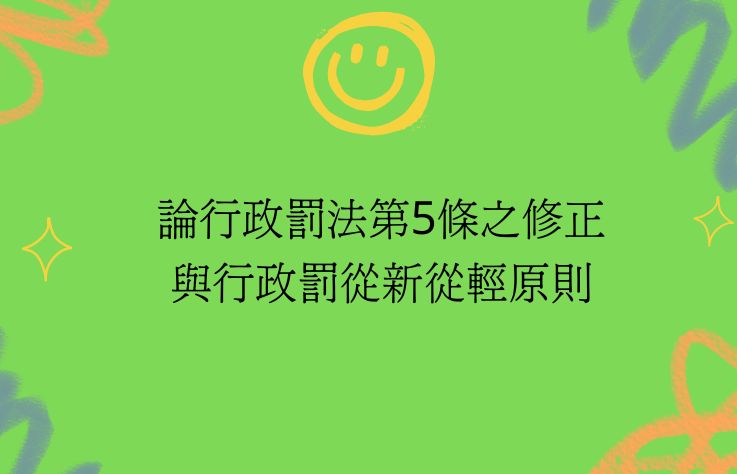#被害人陳述意見 #量刑 #刑事訴訟法 #被害人訴訟參與 #被害人影響陳述
壹、前言
本主題前篇《被害人於量刑中之意見陳述爭議》,已提及被害人陳述制度之梗概及其衍伸之爭議,本文則將著重於研究他山之石——美國被害人影響陳述制度,所能帶給我國之啟發。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7及第289條第2項後段,賦予被害人或其家屬得對科刑範圍表達意見之機會的同時,哪些內容可以「說」,哪些不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貳、被害人影響陳述之內容及其作為量刑因子之正當性探討
被害人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又可被稱為被害影響證據(Victim impact evidence),或是被害影響證詞(Victim impact testimony)。其係指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向法院所為之犯罪對其所造成之身體上、精神上,以及經濟上影響的陳述 。
關於被害人影響陳述的類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Payne v. Tennessee案(以下簡稱Payne案)中,認為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8條並未禁止被害人影響陳述,國家可以參酌關於被害人人格特質,以及犯罪對被害人即其家屬所造成影響的被害人影響陳述 。然而,對於被告以及犯罪的描述、量刑建議是否應予採納,聯邦最高法院並未論及。以下針對不同的被害人影響陳述內容為分析:
一、被害人的人格特質
被害人的人格特質,於Payne案中,法院認為此一陳述的目的是為了顯示每個受害者「作為一個人的獨特性」,不論在多數人眼裡,被害人是不是一個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人,他仍是一個被謀殺的人 。Payne案中多數意見認為應唯一限制的是,該陳述在正當法律程序的操作下不能「過度不利」於被告 。
通常,法院會承認被害人的特質,諸如被害人是「好人」、「殉道者」、「國家認證的鋼琴家」、「每天閱讀和攜帶聖經的牧師」、「高智商的聰明人」、「警察」等等 。其他像是被害人的才能、智能、宗教信仰、工作倫理、教育背景、工作倫理、社會地位等,亦曾被法院認可 。然而,亦有法院(Booth v. Maryland案)認為若將焦點集中在被害人的個人特質和名聲上,將形成一個對被害人個人特質的「小型審判 」,此是一個不被允許的風險 。
然而,被害人的個人特質是否真的會影響法院量刑的判斷?早期的模擬研究顯示,相較於沒有魅力的被害人,被告過失致一有魅力的被害人於死將被科更嚴厲的罪刑,以及倘若被告強制性交的對象是較受人尊敬的被害人,則其將受比強制性交對象為不受尊敬之人更長的徒刑。惟Mazzella等學者對80項研究進行了深度分析,認為被害人的吸引力、種族、社經地位和性別對於陪審員的判斷一般而言是無關緊要的(即並不會造成影響) 。而Burkhead等學者則以模擬陪審團為觀察對象,發現曾聽聞過被害人影響陳述的陪審員,比起未曾聽過的陪審員,更傾向於假設的死刑案件中投下死刑的選項。且被害人的本質亦是重要的:當被害人的職業是警察時,死刑的判決結果會增加,然而若被害人的職業是加油站主人時,結果會相反 。
雖然以模擬實驗的結果來做歸納是不可靠且有風險的 ,然不可否認的是,被害人的特質倘若被過度強調,將容易導致量刑者以被害人的「社會價值」作為量刑基礎。本文亦認為,倘若將關注焦點放在被害人的特徵上,似有變相評價各個被害人的社會價值而忽略其作為一個「犯罪的受害者」的身分,更有甚者,恐會出現類似「社經地位高的人命比較值錢、高尚」的質疑。因此,除非被害人的身分可以清楚證明犯罪情節,或是與加重量刑因素有關,否則應將被害人的個人特質排除於被害人影響陳述之外 。
二、犯罪所產生的影響
犯罪產生的「影響」,會有哪些呢?在Payne案中,法院只談到了犯罪對被害人家屬的影響,但各州普遍允許提出犯罪對社區所帶來的影響。例如,阿拉巴馬州刑事上訴法院允許提出犯罪對整個執法界產生影響的證據,而印第安那州則在被害人為警察的案件中,允許州警察提出因為同袍被殺導致長官無法正常工作,且一些警察開始以暴力非法的方式對待公眾的證據。甚至,喬治亞州最高法院曾允許一個電台call-in節目的聽眾,去證明社區所受到的影響 。
另外,此種「影響」的範圍究竟有多大呢?絕大多數的司法機關幾乎都沒有明確指示「影響」的允許範圍,例如聯邦法律就含糊地規定,控方可以提出有關「被害人及其家屬所受傷害,和損失的程度及範圍,以及其他任何相關信息」的證據 。
在所有形式的犯罪影響證據中,幾乎被無限制地承認,且最有說服力的是與「情感影響」有關的證據。例如,在McVeigh案中,一名四歲女兒的母親出庭作證說,在等待從廢墟中挖出屍體,然後埋葬女兒的過程中,她接到了法醫辦公室的電話。對方和她說,找到了她女兒手的一部分,並詢問該位母親是希望把這一部分手埋在亂葬崗,還是要領回。母親回覆道,她想帶走,這是她女兒的一部分。對於這段證詞,證人因泣不成聲而無法完成,陪審員公開拭淚,倖存者嚎啕大哭 。
此種證據的情感渲染效力,在受過專業訓練的公正法官身上,亦可明顯看出。有法官曾言:「被害人是一個謙遜、親切的人,他會被人懷念。」而在McVeigh案中,連平時沉默寡言的Richard Matsch法官,也在兩天的影響證據調查過程中公開流淚。然而,情感影響證據會使被告面臨幾乎無法克服的難題,亦即無法就該證據提出抗辯,因為此種內在的主觀情感證詞幾乎不會受到交互詰問的影響,而任何挑戰被害人遺族情感損失的真實性行為,都會伴隨著巨大的風險 。
被害人影響陳述,尤其是關於情感影響的相關陳述,具有高度渲染力,在法律與情感並無從輕易劃分的審判實務上,倘若欲使被害人得提出情感影響證據,則在制度的設計上,應盡量避免因此證據地提出而有過度加重量刑的情形。詳言之,具有相類似犯罪情節的犯罪行為,應避免因被害人的陳述能力不同而產生不同結果,而有量刑失衡的問題產生 。
三、對犯罪及被告的描述
此種被害人影響陳述,例如被害人的女兒認為被告是垃圾,或是Booth案中的被害人兒子陳述其父母「像是動物般被宰殺」。因被害人及其家屬本得以證人身分向法院提供關於犯罪情節的細節,法院並得以之為量刑因素,於此證詞和被害人影響陳述的內容並無太大差異,僅係陳述者的身分不同。故而有學者認為,國家並不需為了此種證詞而引進被害人影響陳述制度 。
四、被害人的量刑意見
就我國刑事訴訟法新修正第455條之47 的法條文意而言,其係規定被害人或其家屬可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並於該條立法理由中提及被害人的量刑意見可使量刑更加精緻、妥適。然而,有論者質疑倘若引進此種量刑意見陳述,無論證據是如何謹慎地交給陪審團,都有可能會壓制陪審團做出合理且獨立量刑決定的能力。再者,倘若被害人已提出了對被告量刑的意見,卻被陪審團無視,被害人或其家屬即有可能再次受到傷害 。
而贊成被害人陳述對於量刑的意見者則認為,此種陳述對被害人或其家屬有潛在的治療效果,透過陳述可以使被害人在某程度上掌握被告的命運,這能幫助他們重拾生活的控制權。雖然人們常常認為,與繼續懷有報復和憤怒的情緒相比,仁慈和寬恕的反應更有利於犯罪被害人的心理康復。若是如此,那麼在量刑過程中應給予被害人或其家屬有「份量」的選擇。如果沒有這樣的份量,那麼給予寬恕和不寬恕的選擇基本上是無意義的。換句話說,為了使「選擇仁慈」具有意義,另一種「選擇不仁慈」也必須是有意義的。這意味著應使被害人的量刑意見產生一定的影響 。
本文認為,被害人家屬的量刑意見確有其價值,倘若擔心被害人因本身預期和最終判決結果不一致而有二次傷害的風險,應可藉由法官在被害人陳述意見的前後即先告知被害人家屬,即便他們的意見沒有產生預期的判決結果,此陳述仍在判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降低傷害可能性 。
參、結論
本文將被害人影響陳述分為了被害人的個人特質、犯罪產生的影響、對犯罪及被告的描述以及被害人的量刑意見四類,其中被害人的個人特質和對犯罪及被告的描述,應不得納入被害人影響陳述的內容中。而在處理犯罪產生的影響以及被害人的量刑意見上,亦須小心謹慎避免造成對被告的不公平。
[1] 楊媖淑,《死刑案件之被害影響陳述─以美國法為參照對象》,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頁15。
[1] Payne v. Tennessee, 501 U.S. 808, 111 S. Ct. 2597, 115 L. Ed. 2d 720, 1991 U.S. LEXIS 3821, 59 U.S.L.W. 4814, 91 Cal. Daily Op. Service 5052, 91 Daily Journal DAR 7697.
[1] Supra note 2, at 823.
[1] Supra note 2, at 825.
[1] Logan, W.A. (1999). Through the Past Darkly: A Survey of the Uses and Abuses of Victim Impact Evidence in Capital Trials, 157.
[1] 楊媖淑,前揭註1,頁45。
[1] 例如,被告可能會提出被害人的品格有問題,被害人不受歡迎或被家人排斥的證據,此可能會分散法院的注意力。
[1] Booth v. Maryland, 482 U.S. 496, 107 S. Ct. 2529, 96 L. Ed. 2d 440, 1987 U.S. LEXIS 2616, 55 U.S.L.W. 4836.
[1] Greene, Edie & Koehring, Heather & Quiat, Melinda. (1998). Victim Impact Evidence in Capital Cases: Does the Victim's Character Matter?1.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8. 148. 10.1111/j.1559-1816.1998.tb01697.x.
[1] Greene, Edie & Koehring, Heather & Quiat, Melinda, supra note 9, at 148.
[1] 楊媖淑,前揭註1,頁46。
[1] Talbert, P. A. (1988). The relevance of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to the criminal
sentencing decision. UCLA Law Review, 36(1), 207.
[1] 楊媖淑,前揭註1,頁47;Logan, W.A, supra note 5, at 161.
[1] Logan, W.A, supra note 5, at 162.
[1] Logan, W.A, supra note 5, at 162-163.
[1] Logan, W.A, supra note 5, at 163-164.
[1] 楊媖淑,前揭註1,頁62。
[1] 楊媖淑,前揭註1,頁48;Talbert, P. A, supra note 12, at 204.
[1]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7:「審判長於行第二百八十九條關於科刑之程序前,應予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陪同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
[1] Hoffmann, JL. (2003). Revenge or Mercy? Some Thoughts about Survivor Opinion Evidence in Death Penalty Cases. 540-541.
[1] Hoffmann, JL, supra note 20, at 538-539.
[1] Hoffmann, JL, supra note 20, at 541.